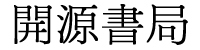陈红民
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
蔣介石與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原题:档案多情似故人——漫谈利用档案研究民国史
转自:《民国档案》2021年第三期
我将近40年学习与研究民国史的生涯,与阅读、利用档案密不可分。不仅利用档案进行研究写论著,也曾整理、编辑与出版过原始档案资料。在地域范围上,不仅有利用海峡两岸档案的经历,还多次赴外国查阅档案资料。
在此,将阅读利用海内外档案,进行民国史研究的体会写下来,与学界朋友们分享。我深知,鉴于学术训练、学术背景、知识结构与学术旨趣各异,每位学者的个体经验或教训均有特殊性,难以复制,但史学研究的基础训练与方法终归有共通性,个人浅见,或能对年轻学者、学生有点启发。
本文拟分享四点体会,分别用四句改动过的古诗词句为标题: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档案”,讲查找档案之态度;二是“既见档案,胡为不喜”,讲用档案之妙处;三是“不识档案真面目,只缘身在档案中”,讲识档案之能力;四是“档案花气清,悠然心独喜”,讲阅档案之乐趣。
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档案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名句,形容寻遍九天之上,穷尽九地之下,决心大、用功勤,仍茫茫不见,所寻不得。史学家傅斯年将其改成“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要求史学家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穷尽可能地搜集资料。我在傅斯年改动的基础上,再引申一步,改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档案”,专为强调找档案的重要性。
傅斯年重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有句“名言”——“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界对这句片面深刻的话一直争议不断,学者们见仁见智,但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谁也不能否认。史学研究是一门实证的学问,所谓“论从史出”,就是指史学研究的结论必须在穷尽所有史料的基础上方能得出。有学者可能偏好理论,擅长分析,做概念史(观念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但其观点终究也要史料支撑。
史料的种类有许多,对于具体的研究来说,各类史料价值是相等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史料是真实可靠的,能用来恰如其分地支撑学术观点,就是好史料。但不能不说,在所有史料类型中,档案资料因具有典藏的权威性、完整性与连续性,很多情况下也有唯一性,所以显得尤为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对“档案”的定义是,“指过去和现在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科技等方面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特别强调了其作为历史资料的属性。学者们写论著、申报课题需要排列“参考文献”时,“档案资料”通常是排在最前面的,这是一种约定俗成。
史学界说到“民国档案”一词,首先联想到的是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它是典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档案的国家级档案馆。多年来,二史馆的研究人员与南京地区高校的教师有密切合作,共同组成了民国史研究“南京学派”,而“史料扎实”,“重视史料,尤其是利用档案资料”正是“南京学派”治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我在南京大学读书、任教多年,导师茅家琦教授、张宪文教授都教导我要注重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特别要珍惜利用二史馆馆藏档案方面所具有的“天时地利与人和”优势。
真正利用二史馆馆藏档案是在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后。我要写胡汉民传记,二史馆有“胡汉民个人全宗”。个人全宗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找到万仁元副馆长,在他的协助下,顺利看到了,并运用到《胡汉民评传》中。万馆长的开明、担当与对年轻学人的支持,终生难忘。此后,我时常去二史馆查阅档案,在研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战时交通运输、国民党五全大会、蒋介石等课题时,均以二史馆的档案为基础史料撰写论著。
二史馆一向注重档案开放工作。我们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得到了二史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在符合政策法规的前提下,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档案资料复制件。
读书时老师们的教诲与早期利用档案的经历,逐渐塑造了我的研究风格,即偏好利用第一手资料选择课题、撰写论文,对寻找档案有异乎寻常的爱好。除了二史馆,我还去过上海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等档案馆,查阅到许多有用的资料,运用到相关的研究项目与论著中。
查找利用海峡对面的档案,也是我的喜好之一。我迄今去台湾学术访问与参加会议14次,每次赴台,都会抓紧时间去“国史馆”、党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档案。2007年,我在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半年,为学生讲授“中国现代史史料”这门课程,曾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国史馆”,专门看了存放蒋介石档案的库房。台湾学者能进库房参观的也是凤毛麟角。我写过一篇介绍在台湾查档案观感的文章,题为“在台湾查档案是怎样的体验”,发表在“澎湃新闻”上,点击量颇为可观。
赴国外访学期间,档案馆、图书馆是我的必选之地。与国内体制略有差异,国外有些重要图书馆也因收到捐赠而典藏珍稀史料,对这部分史料的管理与普通图书不同,更接近档案。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Library)是我访问次数最多,工作时间最长的海外图书馆。受燕京图书馆的委托,我整理并编辑出版了它所珍藏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两套大型资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档案馆,我查阅并抄录了蒋介石日记,也看过宋子文、孔祥熙、黄郛等人的档案,浙大蒋研中心应该是目前抄录蒋介石日记最全的单位之一(尚未抄全)。2002年我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的善本与手稿图书馆(Butler Library),正好赶上那里开放“张学良资料”,有幸成为最早读到该资料的中国学者之一。2010年浙江大学与陈香梅女士达成协议,浙江大学建立“浙江大学陈香梅资料与研究中心”,我受派担任主任。两年后,我与浙江大学档案馆的同仁一起远赴华盛顿,在陈香梅担任主席的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ds)大厦,清点、接受了陈女士捐赠的大批档案,运回杭州。
2004—2005年,我有机会在韩国延世大学访问一年,期间专门去设在首尔的韩国“国家记录院”分院。韩国的国家记录院即是国家档案馆,总部在大田市。我无韩语基础,不能阅读韩语史料,但当时想,韩国曾被日本殖民统治几十年,中华民国政府在韩国有领事馆,或许有中、日文的档案。这个推断是正确的,果然在国家记录院里找到了中国驻汉城总领事馆与日本朝鲜总督府外事科交涉的完整档案,是用中文与日文写成的。
2012年起,我利用去英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访问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查找其所藏的蒋介石资料,收获很大。由于数量太大,我行程又紧,未能完成,就再派同事去继续搜集工作。因为有早期的积累,我的年轻同事2020年申请到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英国驻华大使馆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现在进展很顺利。
2019年,我去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讲学两个月,专程去了罗马的意大利外交部档案馆,与馆方达成了搜集民国时期中意关系与蒋介石资料的共识。可惜,因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此事目前暂时停摆。
我对档案的痴迷与用功,有一事可以说明。1996—1997年,我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去哈佛大学访问一年。其他同期的访问学者多选择学英语,修课程,与美国学者交流等,而我就窝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室,花九个月时间将其所藏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全部录入电脑。那时刚有笔记本电脑,黑白屏幕,分辨率很低,我每天工作下来,眼睛干涩到非常难受,后来有种“眼睛要瞎了”的感觉。等资料全部录完之后,我趴在图书馆的桌子上,无声地流泪哭了,当然也是欣喜的泪。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说,他当馆长这么多年,看过连续到图书馆的读者,是为写博士论文,最长大概是3个月,我这九个月的记录恐怕很难有人打破。当然,这么傻用功,也博得了一些名声,奠定了我后来与燕京图书馆合作的基础。至今,在哈佛燕京学社与图书馆,都还有我当年死用功的传说。
二、既见档案,云胡不喜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出自《诗经·风雨》。是说女子见到期盼很久的郎君,压抑内心狂喜,故作矜持,平淡地说声高兴。我改两个字,用在这里,是说利用档案带来的收获,或者说是意外之喜。
学界普遍认同如下观点:一部好的史学作品,要有“三新”,即能发掘新的史料,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到某项研究或者一篇论著中,同时达到上述“三新”是有些难度,能有“一新”就相当不错。利用档案,探析出新史料背后的意义,就是发掘新史料最常见的方法。
自己的研究,得益于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甚多。我主持整理、编辑与出版了两大套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珍稀资料——《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胡汉民资料从接触到最后出版,前后用了10年时间,蒋廷黻资料更长,前后是13年时间。我以哈佛燕京的胡汉民资料为基础史料,完成了博士论文《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研究——胡汉民的人际网络、反蒋抗日活动及其他》,修改后由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以《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为书名出版(2003年)。蒋廷黻资料的整理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这两套书都获得了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蒋廷黻资料还获得了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用这些资料写成的学术论文,为数不少,在此就不列举。可以说,通过阅读与整理这两批史料,我的研究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天道酬勤,付出有所回报。
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我继承老师们的传统,告诫研究生要珍惜靠近二史馆的优势,多跑档案馆。最初指导的几位博士研究生,就结合我承担《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课题,在五院中各选一个院,如研究行政院、考试院与监察院等,经常到二史馆爬梳档案,他们分别撰写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均获好评,毕业后作为学术专著出版,还分别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项目资助。正是因为有档案史料的基础,他们在史学研究上顺利起步,成了某一课题的专家。
到浙江大学后,失去了利用二史馆档案的便利,我要求学生尽量去浙江省档案馆查阅档案,运用到学位论文中。有位学生协助我整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蒋廷黻资料,她利用这批资料,完成了博士论文,也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青年项目。另一位博士生正在写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美空军合作方面的学位论文,所依靠的资料是他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阅到的“陈纳德档案”。
观察一些近现代史学者的学术生涯,很容易发现他们做学问有个共同的方法,即不自我设限、囿于特定的研究课题,而是随着档案的发掘转入新的研究题目,由档案决定研究主题。这很符合学术界强调的“论从史出”观念,也与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之论暗合。如我的导师茅家琦教授,去欧洲访问时发现一些外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关系的档案,开拓出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这个全新的课题,成果斐然。章开沅教授从辛亥革命史转到商会史研究,后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也独树一帜,是因为他先在苏州档案馆找到完整的苏州商会档案,在耶鲁大学的金陵大学档案中,找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重要史料。杨天石研究员本科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研究兴趣与课题多次转向,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他访问海外的档案机构,要求看人家没有被利用过的馆藏档案,并不限于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找到这些档案后,他再发掘其价值,写文章介绍给学界。杨天石后来汇编成《海外访史录》,书中涉及到孙中山、毕永年、宫崎寅藏、黄宗宪、康有为、胡适等人的档案,多是就一封未公开的信,或一则史料说事。因为是介绍了新史料,所以有价值。
坦率讲,我早年是画地为牢,总把自己限定在研究胡汉民这一课题上,到图书馆档案馆只查胡汉民相关的资料,没有就走人。后来,我见贤思齐,尝试上述前辈学者的方法,先找档案材料,再看能做什么研究。我涉足中韩关系的课题,事先没有任何基础,但由于在韩国找到那批过硬档案,连续写了几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历史研究》《民国档案》等刊物上。对蒋廷黻、陈香梅的研究,也是先有档案材料,再从材料中找研究题目,均发表过较多的成果。
根据我的亲身经验与对其他学者治学路径的观察,有志于近现代史研究的年轻人,如果能耐下性子,抱住某种特定的档案,认真研读几年,一定会有收获的。现在,有些较有成就的年轻学者,也正是这么做的。
所以提倡这种方法,是因为史学研究者,包括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研究生,有一定的阅历,最不缺的就是各种断想式的新想法,但历史是实证的科学,有想法,没史料(或者有史料,但限于条件无法查阅),最后肯定写不出像样的论文来。套用一句时髦的句式,“困在各种想法里却没有史料的博士生。”而有了第一手、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再去找相关研究的成果,找个合适的位置将史料嵌进去,无论是否与之前的研究重合,都会是一篇不错的文章,至少有新材料,为以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我曾经提出过如下的观点:蒋介石档案与蒋介石日记开放后,出现了大批相关的成果,蒋介石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从蒋介石不在历史现场的蒋介石研究,到蒋介石在历史现场的蒋介石研究”。
杨奎松教授告诫自己的研究生,要找些前人没有仔细梳理过和研究过的材料,做自己论文的选材,而去档案馆,“最容易找到这样的题目来做”。
三、不识档案真面目,只缘身在档案中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苏轼人所共知的名句。我改几个字,是要说在史学研究中,对档案史料要沉得下去,也要能跳得出来。
批评“史学就是史料学”说法的人,认为这个论断忽视了史学工作者的分析判断能力与作用,容易造成史料堆砌。我认为,这句话更确切的表达应该是,史学工作者具备了相当的研究能力后,史料就是至为关键的。
传统史学要求好的史学工作者具有史德、史识、史才等素质。如果只要有好材料,好档案就行,那么最好的史学家,应该是档案管理员,他们每天与档案打交道,守着一座宝库。
阅读、处理档案,发掘其历史内涵与价值,恰如其分地将其用在研究中,需要研究者的综合能力。档案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理解历史档案的价值,需要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如档案学、宏观的历史脉络、文件的背景、公私文书格式、书法辨识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知识,面对档案会一筹莫展。而这些知识的获得,除了书本学习外,很大程度上要靠实践,多读档案,认真揣摩,熟能生巧。
在此,说三个我自己处理档案时遇到的事例。
1.对档案价值的判断。同样的档案,在不同人眼里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上海市档案馆曾公布过一批胡汉民秘书李晓生的档案。我阅读后,找到上海市档案馆负责人询问:李晓生这部分档案,是否全部公布了?负责人称,有价值的都公布了,只剩下一个私人帐本,乱七八糟,看不出有什么用。我请他取来一阅,大喜过望,那是李晓生在上海代表胡汉民向北方各省“新国民党”负责人发放经费的记录。胡汉民在反蒋过程中是否组织过“新国民党”,学术界有争论,我从哈佛的胡汉民往来函电中,确认有“新国民党”组织,但既然有组织,就应该有活动、有经费往来等,之前苦于找不到更确实的材料,上海市档案馆这本被认为没有价值的账本,不仅记录了经费往来的情况,而且还证实了“新国民党”在北方各省的分布。
2.字迹辨认,断句与代号的确认。燕京图书馆藏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涉及到许多人的信件,其实是不错的繁体字行草或草书,我缺乏书法知识,有的笔迹非常难认,只能慢慢揣摩、比照,结合上下文一点点地猜。但如果是人名或地名等,完全无法猜,虽然最后多数能释读出来,仍有极少数无法确定。
胡汉民与亲友的往来信件中,为保密起见,用了许多只有通信者之间才能彼此心领神会的暗语或者代号。为了正确地解读内容,必须破译代号所指,否则不但对其内容不知所云,甚至连来往双方是谁都弄不清楚。这是个艰难的挑战。我只能开足脑筋,苦思冥想,终于破解出了绝大部分的代号。这些代号的寓意各不相同:有的是依据人物的某些身体特征,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如同绰号;有的则根据历史上的典故演化而来;也有从原名或字、号的谐音与字形变化而来;有的是借用历史上同姓(或同名)者字号;也有的是用了宅名、书斋名。
如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指称“蒋介石”的代号有八个,分别是门神、门、阿门、庆夫、夫已氏、心馀、草头、某。“门神”一词应是出自《水浒传》中的“鲁智深醉打蒋门神”一句,“阿门”、“门”则是变称或简称;“庆夫”应是取意于“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典故;“夫已氏”系旧式小说中对特定人物的称谓,相当于“某某”;“心馀”,大概是借意清代诗人蒋士铨,字心馀。在函电稿中,蒋光鼐也被称为“小心馀”,取“小蒋”的意思。“草头”则是“蒋”字拆字的上半部分。阅读过程中,破译了代号后,有关函电的内容也就豁然贯通,心生欣喜。
3.阅读、利用档案,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与丰富的想象力,这是对研究者更高的要求。在档案馆读档案,不时会看到一些非常有趣、有价值的档案,但如何将杂乱与碎片化的档案,连缀成可以发表的论文,确实令人头疼,需要作者有丰富的想象力和驾驭史料的能力。如2020年《民国档案》创刊35周年,我想用二史馆藏的档案来写论文投稿,更有纪念意义。我反复几遍认真阅读二史馆提供的“蒋介石资料数据库”档案,这些档案都与蒋介石有关,但散在许多部门的卷宗中,时间与空间分布广泛,每份档案都有点意思,但要找个主题写篇学术论文,份量明显不够。我耐心阅读,各种想法很多,但都觉得写不下去,难以成文,不断否定。
有一组国民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档案,是华侨与外国一般民众给蒋介石的信(多数人因不知如何寄给蒋介石,由国际宣传处代收),信的内容五花八门:有向蒋约稿的,有要蒋照片的,有要到中国找工作的,还有集邮爱好者索要邮票的等等。但这些信件时间集中于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在信中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认识与支持,如果从抗战时期外国民众对中国抗战认识与支持这个角度来处理,不仅可以包含了多数的信件,而且信来源于多个国家,写信者身份庞杂、目的不一这些碎片化的“弱点”,反而可以从代表性广泛的正面去理解,符合“民间外交”的特质。方向明晰后,就顺着这条思路,重新整理阅读档案,最后写出论文《外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37—1941)——以国际宣传处档案为中心》,投稿《民国档案》,得以发表。
四、档案花气清,悠然心独喜
“夜久寂无人,露浓花气清,悠然心独喜”,这是宋代张孝祥的词句,写作者一个人在夜色中赏花,无人打扰,独自占有而心中窃喜。阅读档案,也是一件孤独的事情,应该用享受的心情来做。
前面三点,是从实用的角度,讲如何积极地寻找档案,用档案写文章、申请课题,甚至得奖,晋升职称,来获得学术上有形的进步。第四点是无形的收获,看起来有些虚,但也很重要。
1.读档案是一种修行。换个角度看,在当下中国社会,能有时间有机会读档案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是一种极小众的阅读和探寻体验。寻找档案、查阅档案的经历本身,是静心沉气的修养良法,也是极好的人生阅历和财富。为写论著,做课题,或专门的研究,坐在幽静的档案馆里工作,是一种特殊身份的象征。能使自己在浮燥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个平静的方法,还可以增加知识,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每位有条件读档案的人,应意识到这个“福气”,有“悠然心独喜”而惜福的心境。
2.读档案是“同情地理解历史”的便捷途径。原始档案本身也具有文物性质,端坐读档案,通过当时文件、公私函件、日记等,如同回到历史的现场,观摩前人的作为,甚至窥探他们的个人生活。我在读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读蒋介石日记,它们或是亲友间交往谈心,或是政治密谋,或是个人喜怒哀乐的文字时,有时会有“代入感”,仿佛就站在旁边看他们写,通过涂改与修正的文字,细致地体会他们的处境,甚至是思虑的过程。这是真实的历史,远胜过阅读最出色的文学作品。
原始档案的物理存留方式,也能透露出鲜明的时代信息,与其文字内容映证。如我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读到一组档案,是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致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函,内容多是说办学经费窘迫,要求补贴。竺可桢用的是“国立浙江大学”信笺,仅从信笺的质量眼见一年比一年更差,就能证明当时办学的困难程度。
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教授为指导其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生,曾开设《清代档案》这门课,自编教材,目的就在于让学生通过读档案训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各种基本技能。他的学生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继承了这一传统。柯伟林教授在1980—1990年代,要求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生,一定来中国,到二史馆查档案。即使找不到与论文直接相关的档案,也要接受民国档案的熏陶,感受当时的气氛。
3.读档案,应该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生活的一部分。我去过一些国家与地区,每到一地,档案馆、图书馆是首选,而通常意义上的名胜景区去的并不多。如美国先后去过近十次,总共有超过2年多的时间,但著名的夏威夷、黄石公园这些地方都没去过。有一次内人同行,我抄蒋介石日记感到时间紧,就每天拉她去档案馆帮助抄。她抱怨说,人家到美国半个月,就从东部到西部全境游了,我在美国这么多天,都没出过旧金山地区。
在海外档案馆查档案,最容易遇到学界的同行故友,也会结识新的朋友,相互交流心得,扩大自己的学术网络,增长见识。
观察有成就的史学家,几乎没有不重视档案史料的。对于一个研究近现代历史的学者,如果其学术生涯中(尤其是学术起步阶段),没有一段在档案馆阅读的经历,应该是个很大的缺憾。
查阅档案、利用档案,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我从事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这部分内容抽去,我的学术生涯肯定是干瘪的,将是另一幅样子。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1年第三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