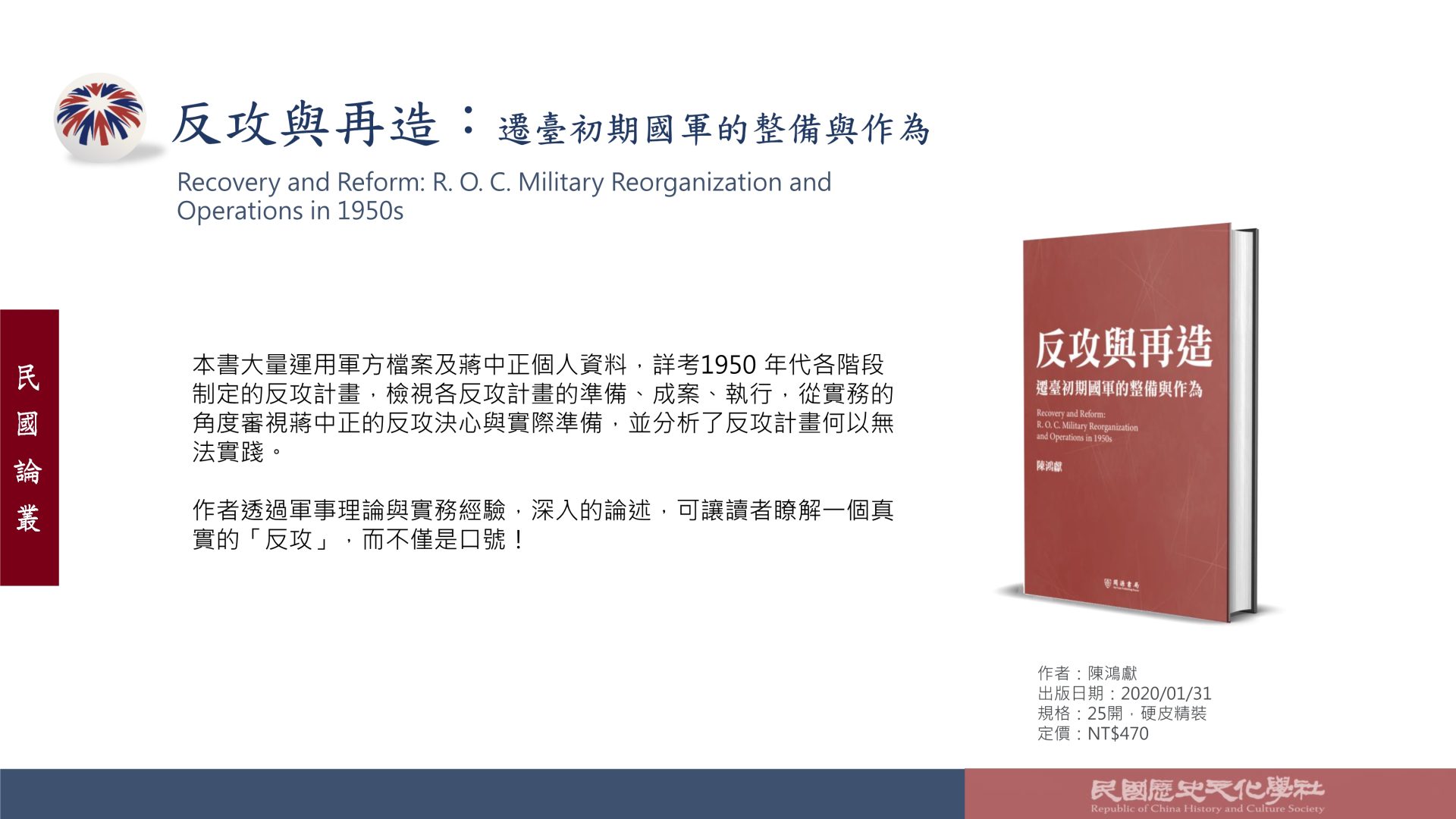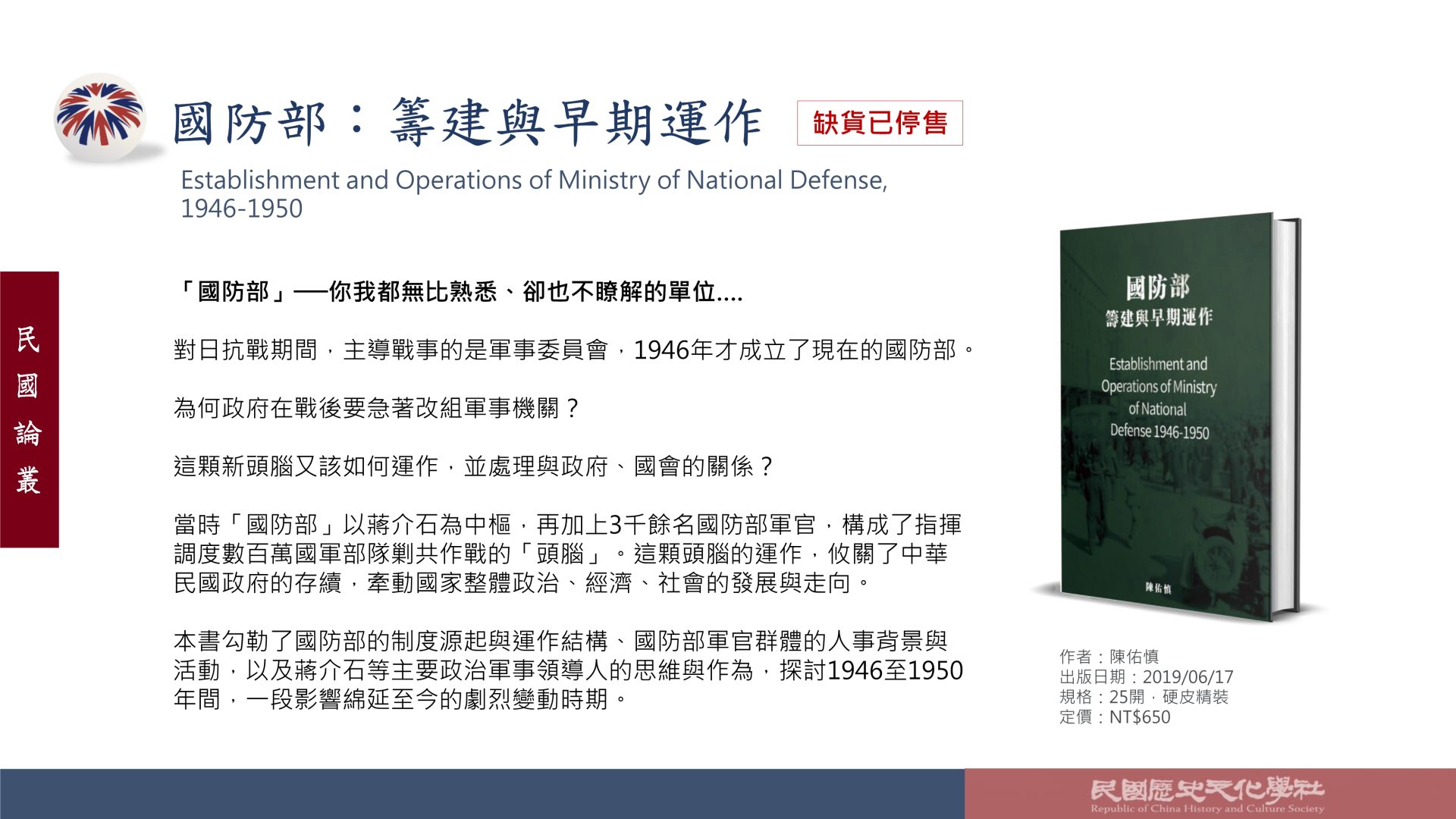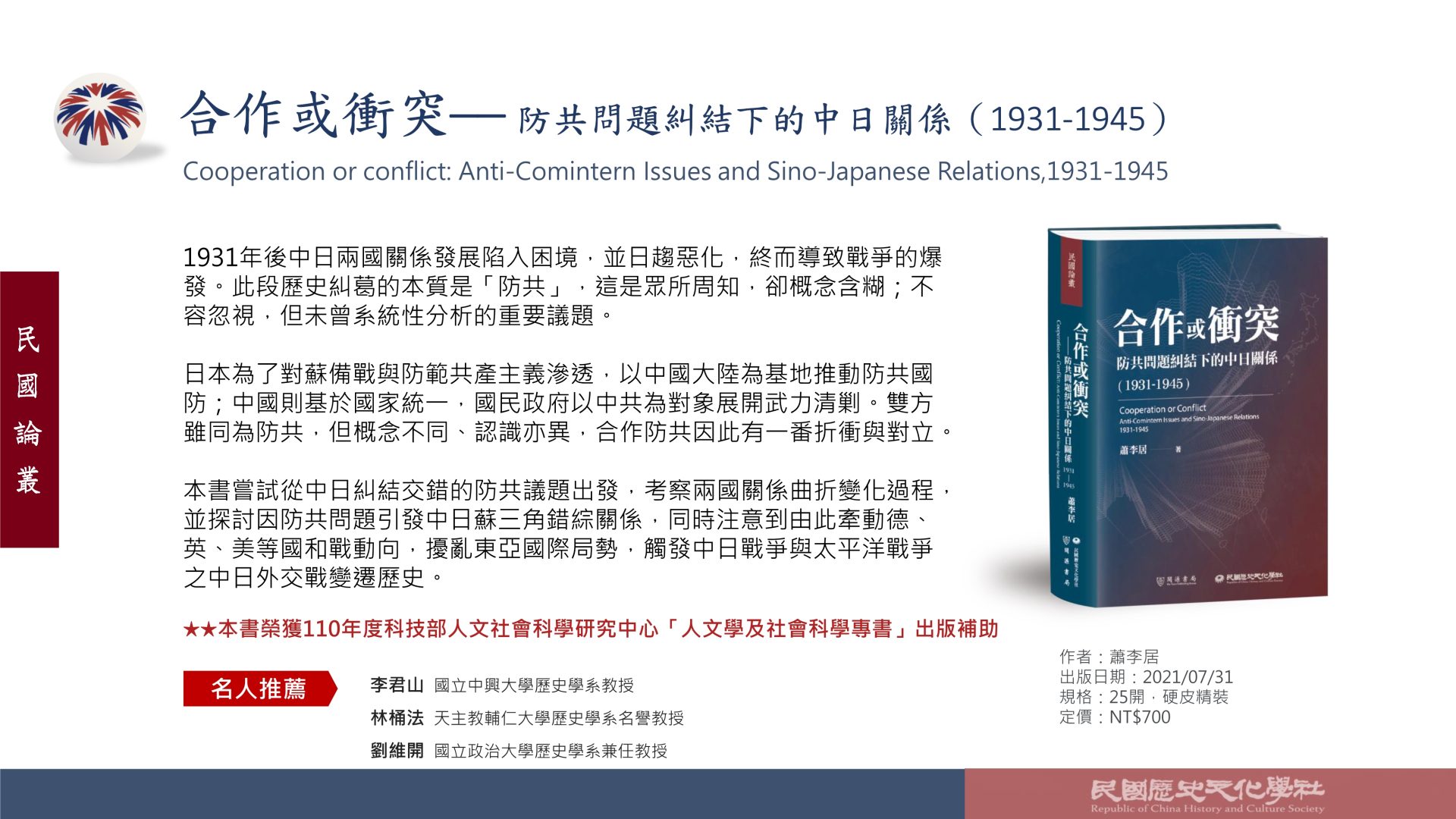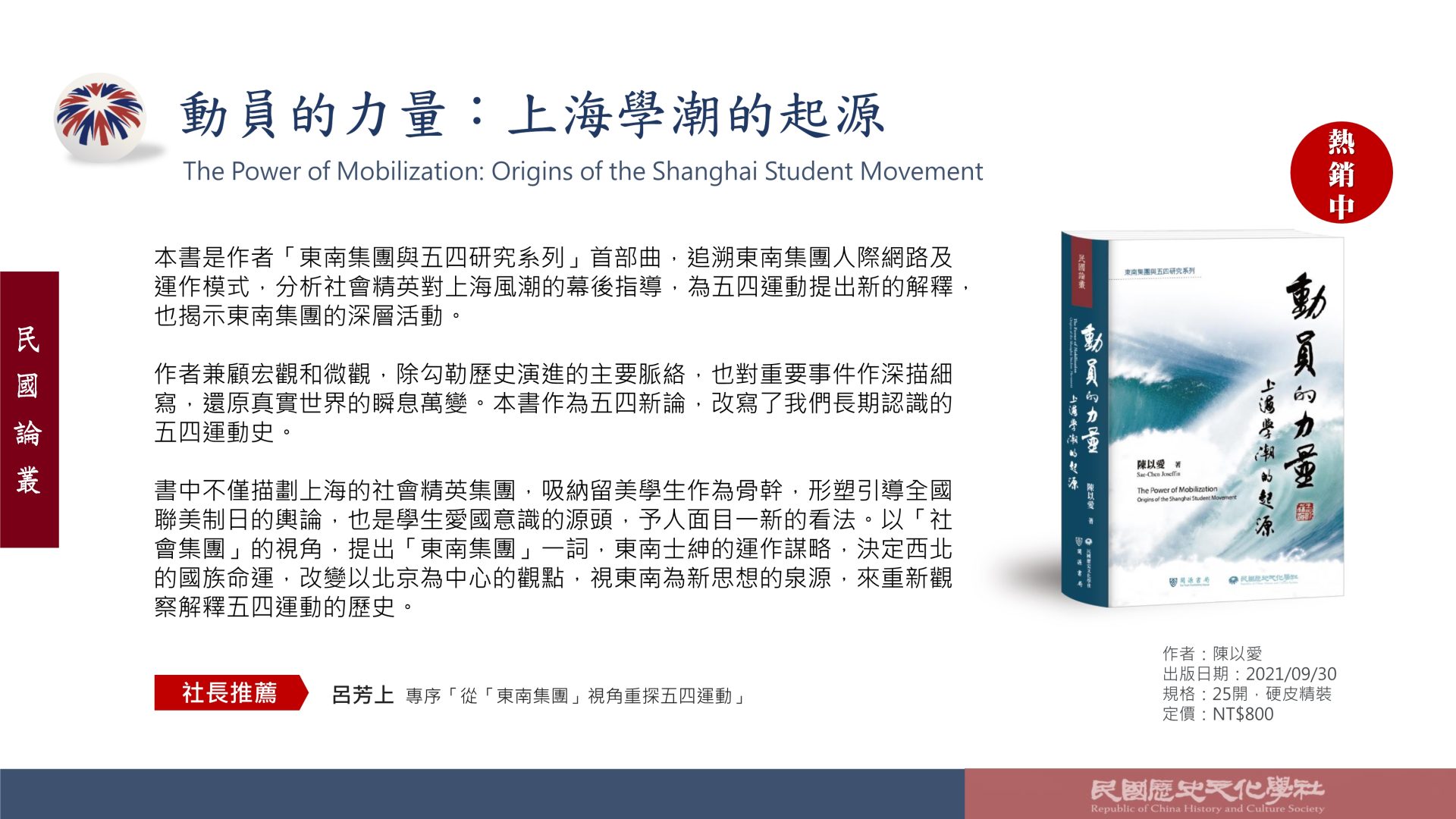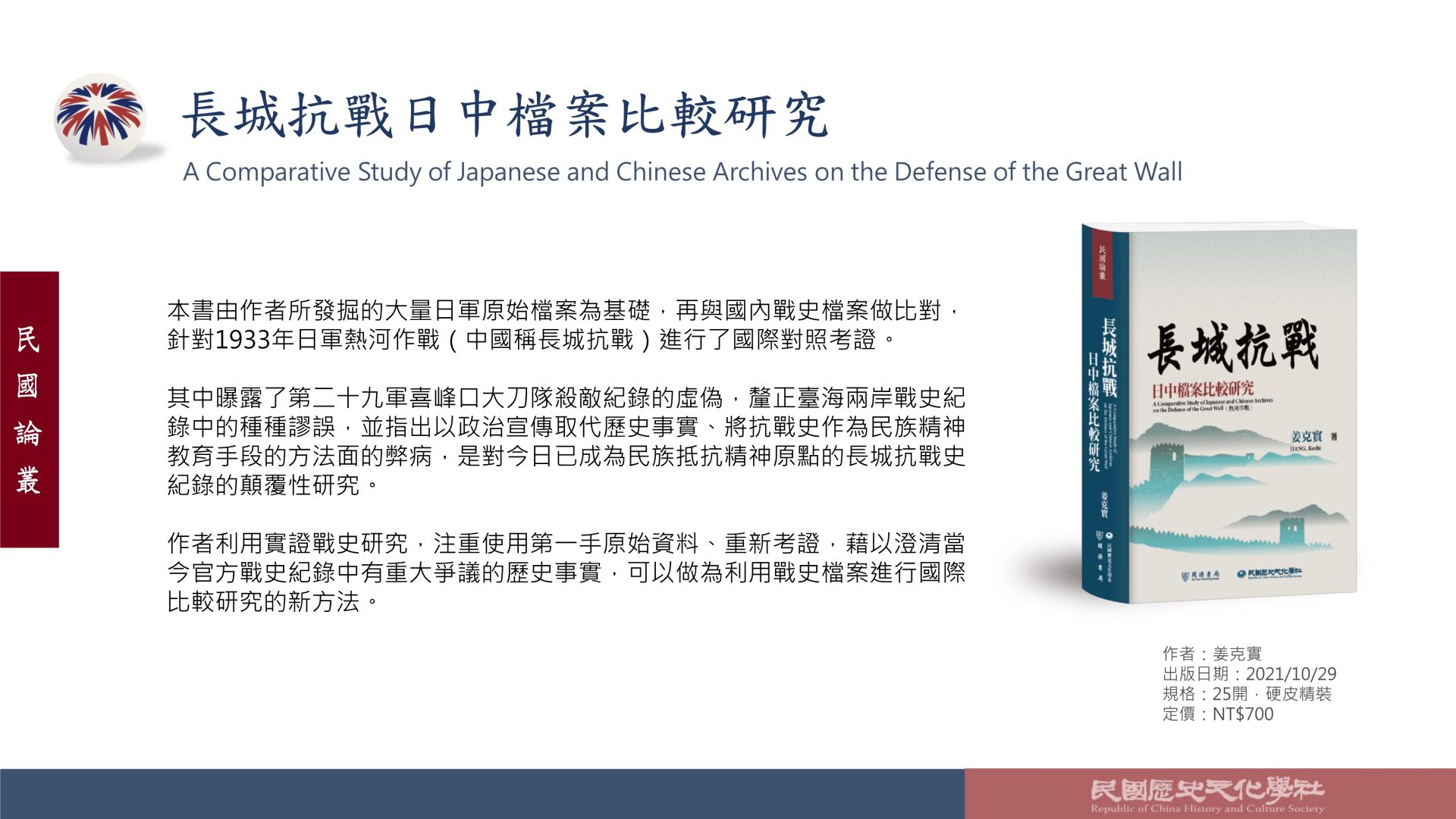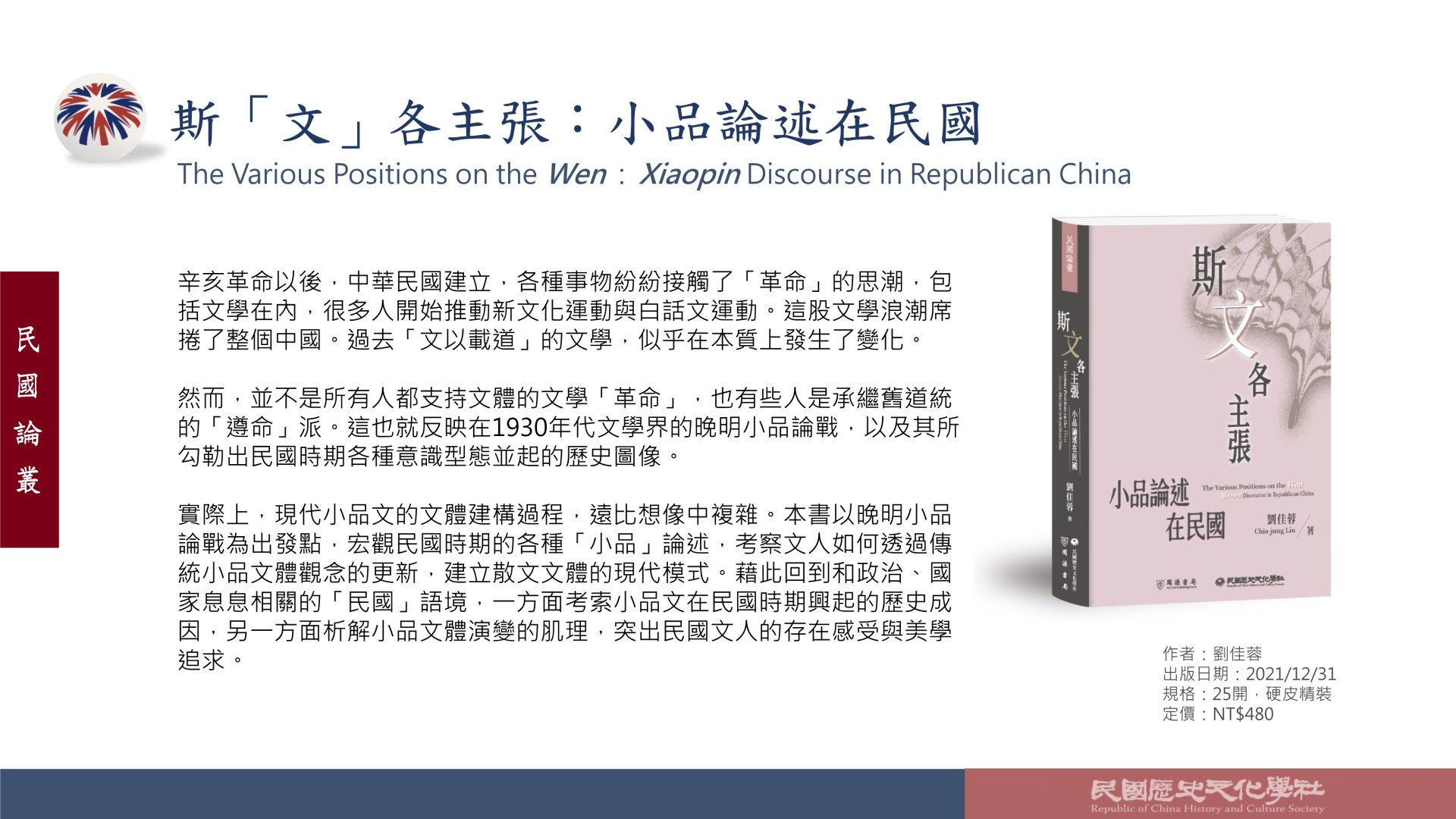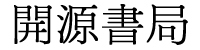1902年,梁啟超「新史學」的提出,揭開了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序幕。
以近現代史研究而言,迄今百多年來學界關注幾個問題:首先,近代史能否列入史學主流研究的範疇?後朝人修前朝史固無疑義,但當代人修當代史,便成爭議。不過,近半世紀以來,「近代史」已被學界公認是史學研究的一個分支,民國史研究自然包含其中。與此相關的是官修史學的適當性,排除意識形態之爭,《清史稿》出版爭議、「新清史工程」的進行,不免引發諸多討論,但無論官修、私修均有助於歷史的呈現,只要不偏不倚。史家陳寅恪在《金明館叢書二編》的〈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中說,私家撰者易誣妄,官修之書多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可見官、私修史均有互稽作用。
其次,西方史學理論的引入,大大影響近代歷史的書寫與詮釋。德國蘭克史學較早影響中國學者,後來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應用於歷史學,於1950年後,海峽兩岸尤為顯著。台灣受美國影響,現代化理論大行其道;中國大陸則奉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為圭臬。直到1980年代意識形態退燒之後,接著而來的西方思潮──新文化史、全球史研究,風靡兩岸,近代史也不能例外。這些流行研究當然有助於新議題的開發,如何以中國或以臺灣為主體的近代史研究,則成為學者當今苦心思考的議題。
1912年,民國建立之後,走過1920年代中西、新舊、革命與反革命之爭,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1940年代戰爭歲月,1950年代大變局之後冷戰,繼之以白色恐怖、黨國體制、爭民權運動諸歷程,到了1980年代之後,走到物資豐饒、科技進步而心靈空虛的時代。百多年來的民國歷史發展,實接續19世紀末葉以來求變、求新、挫折、突破與創新的過程,涉及傳統與現代、境內與域外方方面面的交涉、混融,有斷裂、有移植,也有更多的延續,在「變局」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為史家提供極多可資商榷的議題。194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美國作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說:「過去並未死亡,甚至沒有過去。」(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s not even past.)更具體的說,今天海峽兩岸的現況、流行文化,甚至政治核心議題,仍有諸多「民國元素」,歷史學家對民國歷史的回眸、凝視、觀察、細究、具機鋒的看法,均會增加人們對現狀的理解、認識和判斷力。這正是民國史家重大任務、大有可為之處。
民國史與我們最是親近,有人仍生活在民國中,也有人追逐著「民國熱」。無庸諱言,民國歷史有資料閎富、角度多元、思潮新穎之利,但也有官方資料不願公開、人物忌諱多、品評史事不易之弊。但,訓練有素的史家,一定懂得歷史的詮釋、剪裁與呈現,要力求公允;一定知道歷史的傳承有如父母子女,父母給子女生命,子女要回饋的是生命的意義。 1950年代後帶著法統來到台灣的民國,的確有過一段受戰爭威脅、政治「失去左眼的歲月」,也有一段絕地求生、奮力圖強,使經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醒目時日。如今雙目俱全、體質還算健康、前行道路不無崎嶇的環境下,史學界對超越地域、黨派成見又客觀的民國史研究,實寄予樂觀和厚望。
基於此,「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將積極支持、鼓勵民國史有創意的研究和論作。對於研究成果,我們開闢論著系列叢書,我們秉持這樣的出版原則:對民國史不是多餘的書、不是可有可無的書,而是擲地有聲的新書、好書。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社長|呂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