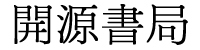——中國社會科學院訪榮譽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
記者:和許多古老學科比較起來,中華民國史還是個比較年輕的學科,您能否談談這一學科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嗎?
答: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不久,董必武、吳玉章等老一輩革命家就提出要編纂《中華民國史》(同時重修清史)。1956年,國家首次將《中華民國史》列入全國科學發展規劃。1971年召開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周恩來總理再次指示,要編纂、出版《中華民國史》。1972年,經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報請國務院批准,通過當時的“出版口”將此項任務下達給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當時的副所長李新接受了這一任務。李新是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幹部,到過延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當過吳玉章同志秘書。有眼光,有魄力,曾組織陳旭麓、孫思白、彭明等編寫四卷本《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革命通史》,獲得好評。他接受任務後即在近代史所成立中華民國史研究組(後改爲室),制訂編纂計劃,采取“來者歡迎”的辦法,吸納了不少所內的年輕學者參加工作,同時,又聯合全國多所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開展協作。今天中華民國史這一學科能發展起來,不能不感念李新的開拓之功。
記者:爲什麽老一輩革命家在建國以後就提出要編寫《中華民國史》?在您看來,建立和發展中華民國史這一學科有什麽樣的重要性?
答:中國有兩千多年的文明史,有悠久的史學傳統。從《尚書》、《春秋》、《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到《元史》、《明史》、《清史稿》,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大量的歷史著作。它們是我們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依靠這些著作,我們民族的生存、發展歷史斑斑可考。從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宣告中華民國成立始,到1949年國民黨撤離大陸,時間不過37年。但是,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段落——一個客觀存在,不可否認的段落。自然,這一段歷史也不可以沒有記載。缺了這一段的記載,我國歷史的發展就缺少了一個重要環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提倡編寫《中華民國史》,其原因我想主要就在這裏。
至于建立和發展中華民國史學科的重要性,我想不外兩方面。一個是學術,一個是現實。
自19世紀中葉起,中國逐漸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人民開始了外抗列强,內謀解放,爭取國家獨立、富强和現代化的鬥爭。在孫中山領導下的建立的中華民國實現了中國國家政體的變革,是這一鬥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則是一個更重要的歷程碑。歷史不能割斷。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是昨日中國有關方面的發展。兩者之間有著切不斷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只有瞭解昨天,才能更好地發展今天,預見明天。我們要建設新中國,就必須瞭解此前的中國,認真清理民國歷史,總結有關的經驗與教訓。隨便舉個例。我們在處理對日關係時,常常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裏所說的“前事”就包括民國時期的中日關係在內。不瞭解民國時期中日關係中發生了什麽?怎樣發生的?如何能發展新時期的中日關係!最近中日兩國外長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會晤,根據兩國領導人達成的有關共識,决定根據“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開展中日雙方的共同歷史研究。其內容包括中日兩千多年的交往史、近代不幸歷史以及戰後六十年的中日關係發展史。這其中的“近代不幸歷史”,就包括民國時期在內。中日關係如此,中外關係的其他方面,中國建設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如此。
建立和發展中華民國史學科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這就是實現民族和諧,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需要。
民國史上,國民黨曾經是革命的、愛國的政黨,有過辛亥革命、反對袁世凱復辟、護法、北伐、抗日等光榮歷史,和中國共産黨有過兩次合作。對于國民黨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貢獻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有助于促進民族和諧,顯示中國共産黨人尊重歷史的光明磊落的態度。去年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胡錦濤同志在報告中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爲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胡錦濤同志在肯定共産黨的抗日將領時,也肯定了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國民黨將領;在肯定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劉老莊連”的同時,也肯定了國民黨人的“八百壯士”。胡錦濤同志的這篇講話在海內外獲得了廣泛的良好的反映。當年我在臺北參加有關方面舉辦的學術活動時,就曾親耳聽到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欣喜地說:“胡錦濤主席也充分肯定我們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了。”
無庸諱言,民國史上,國民黨和共産黨有過兩次分裂,雙方曾刀兵相見,不共戴天,因此彼此之間有許多隔閡、分歧、矛盾以至敵意。研究民國史,對相關歷史作出實事求是的科學的說明和闡釋,揭示歷史真相,剔除其中那些謬誤的、不恰當的、被誤解了的或被誇張了的成分,有助于消除隔閡,化解怨仇,减輕敵意。這一方面,研究民國史的學者大有用武之地。“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近年來,兩岸研究民國史學者已經取得了不少共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一些原來堅持反共的人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
記者:您從學術和現實需要兩方面談到建立和發展中華民國史學科的重要性,很對。但是,從需要出發,人們就可能根據需要剪裁歷史,解釋歷史,使歷史成爲任人梳妝的女孩子。怎樣防止這種狀况,保證民國史研究在最大程度上的科學性?
答:您的這種擔心有道理。歷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還原歷史真實,揭示歷史本來面目,因此,首先要遵循歷史唯物論的思想路綫。恩格斯說過:“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歷史的情况之下才是正確的。”恩格斯的這段話指明了歷史唯物論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則。這就是,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必須是客觀存在的歷史本身,而不是先前就存在于我們頭腦中某種“原則”。自然,中華民國史的研究也必須如此。
舉例來說,辛亥革命時,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怎樣認識這一歷史現象?通常認爲,中國資産階級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密切,有著天然的妥協性,因此,從這一“原則”出發,人們很容易認爲,孫中山讓位一事是中國資産階級妥協性和軟弱性的表現。但是,如果我們從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出發,就會發現,孫中山當時完全懂得,只有排除袁世凱,“堅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才能“斬斷他日內亂禍根”,“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孫中山之所以讓位,主要是因爲革命黨人面臨巨大的財政困難,使得南京臨時政府連維持自身運轉的經費都難以籌措,一直到南北和議簽字前夕,孫中山還在企圖以“舉借外債”的方式解决北伐所必需的巨大軍費。只是在借債無望的情况下,孫中山才忍痛接受和議,讓位于袁世凱。兩相比較,顯然後者比較接近于歷史真實。
人們當然可以根據現實需要去選擇自己的研究計劃,但是,却不能根據現實需要去裝扮、改造歷史。人們在任何時候都要將科學性放在第一位,一切違背歷史真實的成分都要趕出歷史著作。
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不僅是歷史研究的出發點,而且也是檢驗歷史判斷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對于既往的民國史,人們有許多判斷、觀念和看法,它們大都形成于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有的正確,有的不正確。這就要根據客觀存在的史實加以檢驗。正確的要堅持,不正確的要修正,不完整的要加以補充。,
記者:記得您在什麽地方說過,歷史如流水,是已經“消失了的過去”。人們怎樣以這種“消失了的過去”作爲研究的出發點?。
答:不錯。歷史確實是已經“消失了的過去”,看不見,也摸不著了,但是歷史又常常有大量遺存。這就是歷史資料,包括檔案、文獻、實物等。人們正是通過這些歷史資料去研究幷確認歷史事實,重建歷史。
民國時期由于距離現在較近,因此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大量歷史資料。研究古代史,常苦于史料不足,文獻無征。研究民國史,則常常苦于史料太多。據說,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民國檔案能鋪幾十公里長。將全國各地的檔案館、圖書館所收藏的民國檔案、文獻加起來,其總件數也許要以億萬計。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的檔案有八十萬件,蔣介石帶到臺灣去個人檔案約三十萬件,閻錫山檔案有二十余萬件。美國胡佛研究所近年來大力收集民國檔案,除長達五十三年的蔣介石日記外,宋子文檔案有六十余盒,孔祥熙檔案,陳立夫檔案最近也已成爲該館館藏。要研究民國史,這些檔案都必須利用。近年來,我曾五赴日本,六赴美國,七赴臺北,目的大都在于收集和研讀民國檔案,但是所讀仍然很有限,真可謂“渺滄海之一粟”。爲了研究抗日戰爭期間孔祥熙和日本方面的秘密談判,我曾先後訪問過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日本外務省史料館、國會圖書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以及臺北“國史館”等處,才收集到比較齊全的資料,從而得出孔祥熙是國民黨內汪精衛之外的最大主和派的結論。胡喬木同志曾經提出,歷史研究要掌握相關的全部資料。這一點對民國史研究者說來可能很難做到,但仍然要盡最大可能,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資料。
記者: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掌握資料對于歷史學家的重要性很好理解,但是,資料有真有假,利用假資料,其結論不就大錯特錯了嗎?
答:是的。充分掌握資料之後,必須以辯證的方法進行檢驗、鑒別、考證和分析。有些資料,看上去是鐵證,其實靠不住。我舉一例,許多資料都記載,武昌起義時,立憲派首領湯化龍一面表示擁護革命,出任湖北軍政府總參議,但同時却秘密串連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時、布政使連甲、鴉片商李國鏞、清軍第八鎮統制張彪的弁目張振標等多人,密電清廷,要求出兵鎮壓。衆口一詞,言之鑿鑿,而且有柯的文案林某作證,因此歷史學家們將湯化龍定爲反革命兩面派。然而,此說有一個明顯的破綻,即湯化龍、連甲等有身份、有地位的官紳怎麽會在向清廷上書時,邀請鴉片商、弁目等一類人物聯名?循此考索,破綻愈多,幷且最終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裏找到了連甲以個人名義打給清政府的電報,終于證明,此事與湯化龍無涉,爲湯摘掉了“反革命兩面派”的帽子。
民國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因此歷史學家必須十分謹慎地使用資料。特別須要警惕的是,不對紛紜歧异的衆多資料作全面的、辯證的考察,就輕率地取己所需,這種情况,常常會造成對歷史的誤判和誤斷。
記者:聽說民國史學科剛剛建立時,由于“禁區”多,“雷區”多,因此許多學者不敢踏入這一領域,有“險學”之稱。過了若干年,研究者愈來愈多,又成了“顯學”了。是不是這樣?
答:是這樣。民國史學科初建時,反對的人、想不通的人頗多,還有人主張解散剛剛建立的民國史研究組。但是,當時李新頂住了。他說:我們是根據中央的指示開展工作的。你們要解散,拿批件來。反對的人拿不出批件,自然,民國史研究組照常工作。在逐漸做出了成績以後,原來反對研究民國史的人也就不反對了。此後,研究民國史的學者愈來愈多,原來害怕涉足這一領域的人逐漸解除顧慮,研究的範圍也愈來愈開闊,民國史確實從“險學”變成了“顯學”。
儘管如此,幷不意味著民國史的研究沒有任何危險了。習慣成自然。有一些錯誤觀念,是人們在多年中積澱下來的,不容易一下子改變;也有個別人還不習慣于通過“百家爭鳴”的辦法去對待學術上的不同認識,因此,我覺得,要進一步發展民國史學科,還需要不折不扣地堅决貫徹“雙百方針”,建設寬鬆的有利于學術創新的環境,鼓勵大家坐下來,深入地掌握資料,深入地進行研究,我想信,民國史學科必定有一個大的發展。
記者:您談到上一世紀七十年代,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國務院“出版口”將編寫《中華民國史》的任務交給了近代史研究所,現在這個任務完成得怎樣了?
答:當時,我們計劃寫三部大書:1.《中華民國史》12卷,2.《民國人物傳》12卷,3.《中華民國大事記》39卷,4.《中華民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文化》(專題資料)600題。三十年來,我們在人力、財力嚴重不足的條件下,兢兢業業,精益求精,至目前止,《中華民國大事記》和《民國人物傳》都已出齊。《中華民國史》已出版8卷,另4卷初稿亦已完成。已經出版的部分,受到國內外學術界,包括臺灣學者在內的廣泛好評,被認爲是資料翔實、嚴謹求實、風格清新,具有高度學術水平的著作。但是,已往編纂工作也存在較多不足。其一,上述著作,成于三十多年中,出于多人之手,有加以修訂、統編的必要。其二,近年來,大陸、臺灣以及英、美、日本、俄羅斯所藏民國時期檔案大量開放,有進一步加以利用的必要。其三,編纂計劃制訂于三十多年前,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我們的認識水平,現在看來,還存在較多缺陷,例如,原計劃以反映民國時期統治階級的歷史爲主,以政治史爲主,而未能充分反映民國時期的歷史全貌;又如,缺少中國歷代史書必不可少的“志”與“表”等重要體裁。其四,因人力、財力不足,《中華民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專題資料)在出版近50種後即行夭折。上述不足,倘不加以克服和彌補,那末,它將很難成爲代表國家和時代水平的學術巨著。借用孫中山的話來說: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年12月14日